| 古印度文明的发现:Archaeological
Ruins at Moenjo-da^ro and Harappa |
|
1-0-0. 印度文明曾经出现过的断层:The Ancient Sindhu-Saraswati^ Civilisation。
 在20世纪20年代前,印度历史被认为
是从约1500BC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时开始。 在20世纪20年代前,印度历史被认为
是从约1500BC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时开始。
但是,拜现代科学考古,人们才知道,在那之前,约2500BC已经有了深深影响后世的文明,在今巴基斯坦地区。例如山冈上的Mohenjo-da^ro,
出土遗址中有一座被许多房子围绕着的卫城,大概是宗教人士和朝臣们用的。在遗址上发现了许多人工制品,包括陶器、金属品和珠宝。还发现了印章刻着牛等动物
、树木和文字。印度古文献中竟然从未提到过这些。Harappa与Mohenjo-da^ro遗迹的文明被称为“Harappa文明”或“Indus
Civilization”。在發現Sarasvati河的遺迹後,"Indus
Civilization"的名稱更新为"Sindhu-Saraswati^ Civilization"。另外遠離印度河有兩個遺址,一是Lothal,二
是Dholavira,虽不属于这兩河的流域,但其出土遺物显示兩個遺址也属于Harappa文明,在年代上
稍晚于Harappa城。
1-0-1.
考古工作的进行
这古印度文明的發現,早在1870年由英國Charles
Masson, Alexander Burnes, Sir.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開始發掘。进入二十世紀,
挖掘工作在Harappa由Rai Bahadur Daya Ram Sahni繼續,在Mohenjo-da^ro由R.D.Banerji继续。终于在1925年,考古学家宣布发现印度河流域上这两大城市遗址: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内拉尔卡纳县城南20公里处的Mohenjo-da^ro和旁遮普的蒙哥马利县的Harappa。
 印度河流域遗址中首先发现的是最大的Harappa。Harappa位于Sahiwal(距拉哈尔约250公里)西南35公里处,遗址发现于1920-1921年,规模比Mohenjo-da^ro遗迹要大,但是地上部分在修建拉哈尔和木尔坦之间的铁路时被破坏。幸免于难的一些公墓则向世人揭示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文化。Harappa与Mohenjo-da^ro考古遗迹的近似,像是2000~1700BC的姊妹城。这里以农业和贸易为主要的经济来源。Harappa位于Ravi河畔,在此进一步出土了一些更早的(前哈拉帕文化)的文物,它们与果德迪吉(Kot
Diji)出土的文物就极为相似。 印度河流域遗址中首先发现的是最大的Harappa。Harappa位于Sahiwal(距拉哈尔约250公里)西南35公里处,遗址发现于1920-1921年,规模比Mohenjo-da^ro遗迹要大,但是地上部分在修建拉哈尔和木尔坦之间的铁路时被破坏。幸免于难的一些公墓则向世人揭示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文化。Harappa与Mohenjo-da^ro考古遗迹的近似,像是2000~1700BC的姊妹城。这里以农业和贸易为主要的经济来源。Harappa位于Ravi河畔,在此进一步出土了一些更早的(前哈拉帕文化)的文物,它们与果德迪吉(Kot
Diji)出土的文物就极为相似。
Mohenjo-da^ro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旅游胜地。1921~1922年R.D.Banerji在印度河干流的沙丘上发现了“奇怪的史前遗物”,经过进一步发掘,一个大约4500年前
青铜时代的古城遗址出土了。城址占地约8平方公里,规划得像一张棋盘,每个住宅都有6至10间房、院子,所有建筑都用红砖砌成。全城有一套完整下水道系统。该城按发掘地势高低,大体可分为上城和下城两部分。一到上城,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高达15米多的圆形古堡。在古堡的下面,是4500年前建成的城市。从古堡往下走,是著名的大浴池和粮仓,大浴池由红砖和灰浆砌成,四周还有精巧的上下水道。印度河文明专家认为,这座大浴池很可能是宗教仪式
用的,乃至现今印度河地区仍留着沐浴仪式传统。下城离上城约1公里,最使人惊奇的是许多房子里都有倒垃圾的滑道。
1980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Mohenjo-da^ro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届会议报告所评定)。
直到今天印度河文明的發掘工作從沒停止,甚至還發現了另一條古河道,河道兩旁
又發現很多古遺址。在廿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參與此事,與巴基斯坦成立了美巴考古協會。
Dr.Paolo Biagi在1995年開始在印度從事考古工作,在Rohri
hill地區發現了很多Harappa的石器,有些石器甚至有十萬年之久。Dr.Jonathan Mark
Kenoyer教授是Harappa考古研究計劃的副董事長,現在仍然在哈拉帕遺址中進行考古工作。Dr.William Rbelcher考察印度河流域海邊,發現了公元前哈拉帕漁業的証據。
最近在Harappa的挖掘工作由美国The Harapp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团队于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of
Pakistan合作,开始于1986。
|
|
1-0-2.
考古遗迹的位置与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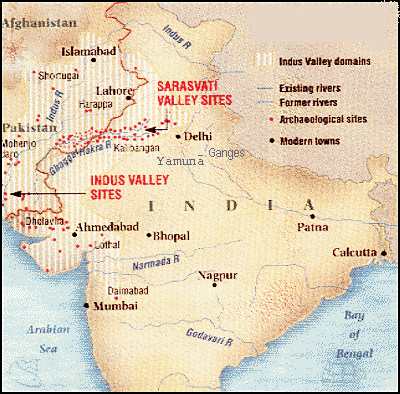 对于Hrappa文化起止时间,说法不一。学者惠勒考古断定为2500BC~1750BC年。另科学家阿格拉瓦尔借由碳14定年相结合,断为2300BC~1750BC。 对于Hrappa文化起止时间,说法不一。学者惠勒考古断定为2500BC~1750BC年。另科学家阿格拉瓦尔借由碳14定年相结合,断为2300BC~1750BC。
经过对Mohenjo-da^ro的三个古城遗址的发掘,发现其历史分期为上下数层。历史最早的一层约当于公元前3300年,其次是约公元前3000年,最晚的一层约公元前2700年。从遗址地基的坚固性,建筑规则的整齐性来判断,证明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此文明已经
相当社会化--有成熟的文化体系。
印度有如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三面环海,一面靠山,虽然有着天然的封闭地理环境,但西北部的山脉并非不可逾越。所以许多世纪以来,军队、商人和朝圣者络绎不绝。而印度境内地形复杂,
各地环境悬殊,因此,往往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互动,超过印度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在远古,来此的人都是穿越西北面的山隘,开创印度河文明的人
也是穿越这些山隘而来。
由地形图可以看出,在Harappa^文明时,从印度河流域去两河流域,可能比去东印度的恒河地区还要方便。
所以东西印度的先住民文明、文化与种族,应该是多样的,虽然笔者将此时的非新入侵的雅利安人都统称为先住民。
|
|
|
|
根据考古发现,古代印度奴隶制国家可能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因为Mohenjo-da^ro和Harappa两座城市都是有精心规划设计的。这两座城市拥有宽阔的道路和良好的排水系统。它们的发达程度要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它城市。  Mohenjo-da^ro遗址中的大浴池
,长11.7米-宽6.9米-深2.5米。可能是当时举行宗教仪式时,供信徒沐浴使用。 Mohenjo-da^ro遗址中的大浴池
,长11.7米-宽6.9米-深2.5米。可能是当时举行宗教仪式时,供信徒沐浴使用。
 Harappa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三层建筑物的遗迹。 Harappa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三层建筑物的遗迹。 |
Harappa,Mohenjo-da^ro包括附近的Rohri,都是印度河流域,也是薩拉斯瓦蒂河流域的下游
。此外较知命的还有兩個古遺址: Dhoravira和 Lothal。
Dholavira是1967-1968年間在Khadir島上北方發現的古城遺址,這遺址在1989年正式由考古學家J.P.Joshi開始發掘,城分三部份,一是統治者所住的衛城(Citadel),二是中城(Middle
Town),三是低城(Lower
Town),這裡有很完整的城牆,現在看来似乎是缺水的島上荒漠,其實在古代是有河流的,科學家利用人造衛星探測到河流是變成了地下河。Dholavira四週有很多水塘殘跡,考古學家在這裡發現了一個263x39x24英呎巨大水塘.考古學家從發現的遺物研判Dholavira城的中央是工廠,是做珠鍊的工廠,質地是光玉髓,顏色多樣化,有色澤,打磨後有光澤,專家們認為,這些珠鍊經過巴林再轉銷到兩河流域,這就是為甚麼在兩河流域許多古墓裡會發現有很多古印度河流域最常見牛紋印章的原因。

Lothal雖然遠離古印度河,可是也極受Harappa文明的影響,遺址裡的建築物所用材料与風格是和Harappa遺址一樣的.最初這個遺址被發現時,考古學家們猜測最上一行左二圖是修理船隻的船塢,所以才想像出左一圖來,結果呢?原來錯了,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原來是水塘,對了,是儲水用的大型水塘,整個古城周圍都是大型水塘,用來在雨季時儲存雨水之用,要儲存足夠的水供給全城全年的生活及灌溉之用,不簡單吧?
Harappa^与Mohenjo-da^ro两城相关的范围很广,西起苏特卡根—杜尔(距伊朗东境仅约40公里)东至阿拉姆吉尔普尔(德里附近)北起罗帕尔,南至纳巴达河以南的巴格特拉尔。东西长1550公里,南北长1100公里,范围是今天巴基斯坦的三倍以上。两座城市大小相等,周长大约有4.8公里,面积约85万平方米,居民估计有7万人。两座城市都是由位于高冈上的卫城(统治者的居住区)和较低的下城(居民区)两部分组成。卫城周围环绕着雄伟的砖墙,城墙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方形棱堡,城市建筑规划整齐,主街又宽又长,其中Mohenjo-da^ro的主街宽达10米,在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便备有点灯用的路灯杆,方便行人夜间行走。两座卫城的房屋大多用烧砖建造,城市富人还建有高楼大厦,家中有完整而复杂的排水系统,这一切都显示出哈拉巴文化城市设计的高水平。 |
|
1-0-3.
出土的物件--媲美华人甲骨的“Harappa文明印章”
 2000BC-1750BC印度河文明由衰落而骤灭,可能因为印度河改变了河道,城市周围土地发生干旱,农业破产,加上Ayran压力,所以Mohenjo-da^ro城市文明就结束了。 2000BC-1750BC印度河文明由衰落而骤灭,可能因为印度河改变了河道,城市周围土地发生干旱,农业破产,加上Ayran压力,所以Mohenjo-da^ro城市文明就结束了。
城市的建筑物和街道是用焙干后的泥砖建造的。泥砖的规格相同,这说明它们是用模子造出来的。许多街道有地下排水道。
一枚Mohenjo-da^ro出土的印章,刻着一头背隆成弓形的公牛。在美索不达米亚曾发现过类似印章,推测当时商人们把印章盖在货物上作为出口标记。印章铭文可能就是货物所属商人的名字。 |
1-1-1. 印度河先住民文明的精神内涵
Mohenjo-da^ro城市文明程度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其规划之严谨完善,甚至可以媲美现代化都市。城市的中心部方圆约5公里竟然就可安置3万以上的居民。异於绝大多都市(甚至现在的名都)的是这座古都的建造是有完整城市规划的!城中每户人家都有下水道设施,二楼冲洗式厕所的水可经壁中的土管排入下水道,有的人家甚至还设置了经高楼投掷的垃圾筒。
Mohenjo-da^ro遗迹共由7层都市组合而成,最上层和最底层的建造方式却全然相同,因此,只能认为这座城池是以完整的形态,一举出现于印度平原之上的。
第一位前来从事挖掘工作的马丁·夏尔惊叹说:"简直就像几千年前从未知世界中搬来的一样。"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Mohenjo-da^ro迥异于其他文明遗址---它没有宫殿或神殿的遗迹,但却有着坚固的城塞和十分考究的公共浴场。
城塞虽已遭到严重的侵蚀,但仍可辨认出一些用在特殊目的设施:一扇大门,环绕着城塞的了望塔和棱堡,此外,山麓之上,面临印度河的地方,竟有一座与之相通的港口。
山岗上坚固的仓库里可以存放足够的粮食,一个巨大蓄水池可以满足居民们的生活必需,在它们周围、又紧密地修建了一圈以坚固为首要特点的非常厚实的建筑物。
可想而知,城塞之中不只是人们议论市政、经济和学术问题的地方,在这里,人们需要的首先是安全,所有的设施都纯粹是为了实用而建造的。因此,只能将此地视为遇有紧急情形时供数万居民前来避难,并加以捍卫的场所。
根据其设计来推测,
建造这座古城的动机并非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抵御不安恐惧。那么,而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古代,什么样的威胁迫使人们建造如此大规模的避难所
?可能当时就有强大外敌的存在。所以,即使当时的文化,也不是今人幻想中知足太平的古风。
Mohenjo-da^ro和Harappa的遺址發掘,證明约3000~1500BC的印度河文明已經使用青銅器,大多從事農業、畜牧業,已有象形文字。(Kenoyer,2000:184)普偏的宗教信仰是地母神、動植物(例如牛)、生殖器和祖靈等的崇拜,浸浴和土葬是重要儀式。有些出土的印章、泥板上有修行跌坐和冥想等形象,這些宗教信仰實踐與後世的s/iva崇拜和瑜伽修習等可能有关。(Kenoyer,2000:184)目前许多印度学学者确认这是Dravidians所主导的文明,但也有反对者。(李志夫,1995)根据人种学、语源学与文化人类学分析,印度文化至少已可溯源到Proto-Australoids的母系社会文化,它影响、形成了其后的Dravidians的女祭师制度,对于印度此后的民族融合留下有力的种子。(李志夫,1995:18)
在Aryan入侵前的印度河文明中,父权可能不占统治地位。
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印度这块土地确曾有好些种族在这里定居过,印度最早的开化种族之一是达罗毗荼人(Dravindian),哈拉帕文化的创造者达罗毗荼人,他们皮肤黝黑,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已经熟练地使用金属,制造富于艺术感的陶器,建筑房屋和堡垒,并已经出现富裕的城市,在达罗毗荼人境内,农业繁荣,他们拦河筑坝,进行灌溉。并且不怕横渡海洋去经营商业。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达罗毗荼人仍处于母系社会,崇拜母神及各种鬼神,不曾有种姓制度,
后来,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的大部分达罗毗荼人。入侵者是白种人,自称“雅利安”意为高贵者,以区别达罗毗荼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武力扩张,雅利安人逐步征服了整个北印度。
随着雅利安人的入侵,达罗毗荼人接受了征服者的文化和宗教,但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达罗毗荼人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的许多要素都有意无意为雅利安人所吸收了。原来被达罗毗荼人所祟拜的“鬼神”,被婆罗门人信奉,并给予新的称号,使这些鬼神与正统的印度教的男女天神等同起来。在古代,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常常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然后逐渐接爱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进而被同化。当时的印度也是这样,雅利安是游牧民族,他们生性骠悍,能征善战,达罗毗荼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入侵印度后,雅利安人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先进文化,由游牧转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并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
研究任何时期的印度思想都必须了解,对尔后印度文明具有重大影响的古代殖民印度的两民族,Aryan为主流,Dravindian为暗流。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度先住民,通常认为是现居南印的Dravindians的祖先。虽然目前还不能清楚描述出当时的宗教,但从考古遗迹可以断定当时的宗教有几个特征:
一、似乎属于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人们崇拜石头、树木和兽类等,认为它们是善良的或邪恶的精灵的依附物,具有灵性和某种能力甚至神力。这充分表现在印度河印章上,印章上“反复出现的公牛形象和怪诞多头或身首相异的动物形象几乎可以肯定是宗教象征。”(参见叶公贤、王迪民编著:《印度美术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在印度河印章上,牛的种类最多,有公牛、牛、水牛和野牛等,而后的印度教徒视牛为神的也许与这时期的信仰有关。
"最新的研究顯示,這些符號中有些在日後正式的印度字母表中保留了下來,和公元前約3500年刻在陶器、泥版上的美索不達米亞語符號,以及公元前約3200年刻在陶器、泥版上的埃及語符號,幾乎一樣古老(後面兩種語言符號後來分別發展成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Jonathan
Mark Kenoyer, 2003, 黃中憲譯,
"找回失落的印度古文明",
《科学人》2003年8月號,台北)

|

Molded terracotta tablet
from Harappa showing a man killing a bull with a spear while a horned
figure looks on. Could this depict a sacrifice?

A horned figure rises from
a tree (upper left) while a similarly horned figure kneels in
supplication. At object which some observers have suggested may be a
human head rests on a nearby stool. A giant ram appears in the upper
right and a procession of 7 figures with skirts, plumed headdresses and
bangles stand by at the bottom. Who are these figures? Could this be a
sacrifice? A royal procession? |

Reverse side of the tablet,
showing a female figure grasping two animals by the neck.
A wheel appears above and an elephant below.
Who is she? |
二、似乎有对“女神”的崇拜:在考古遗址中,有大量的赤陶质“女神”像。印度河印章上也有不少女人像,其中有个图像是从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长出一颗植物,很可能是象征大地女神。这种“女神”崇拜与后来印度教的Sakti崇拜(即性力崇拜)可能有关。
三、对应“女神”崇拜的“Linga”(男性生殖器)崇拜:考古学家除在文明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酷似Siva Lingam的石头断片外,还发现了一个用石灰石雕刻的不完整的男性躯干像,其身体扭曲的姿势使人联想起印度教湿婆大神的造像。该雕像的两腿连接处有一个颇大的空洞,可见其上曾有过一个竖起的巨大Linga。这显示当时Linga崇拜已经存在,而为后世印度教文明所继承。
四、S/iva崇拜:在一枚印度河印章上,一个男性修行者端坐中央,似乎正在修炼瑜伽或禅定,形象具有后来印度教神像的风采。该修行者有一个正面和两个侧面的脸,头上戴着硕大的牛角形头饰,使人想起S/iva的瑜伽
士形象和三头标记。围绕着各种动物,这与S/iva的“兽主”的称号也不谋而合。
“四吠陀”中的前“三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主要是吠陀教的,而第四吠陀《阿达婆吠陀》则主要是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时期的宗教的。
《一切经音义》卷二三(T54, P451b)∶“达利鼻荼┅┅其国在南印度境,此翻为销融。谓此国人生无妄语,出言成咒。若邻国侵迫,但共咒之,令其灭亡,如火销膏也”。
1-1-2. 印度河先住民文明的毁灭
这个古老文明究竟是怎样毁灭的?印度的史学家根据遗址和遗物从中提出了种种假说,较有影响的有:
地质和生态变化骤灭说:证据是可考的印度河床改道。由
导致改道的可能原因(地震、生态破坏或其他)以及改道所可能引起的水灾等灾害,都会给古城文明带来巨大破坏。《百道婆罗门诵》所载的当洪水毁灭世界之时,只有人类的始祖摩奴一人在神鱼的启示和帮助下造船得救,也许就是对印度河文明毁灭的一个回忆。
外族入侵骤灭说:论据是,约1750BC印度河流域的
这些城市遭到骤然破坏,特别明显地表现在Mohenjo-da!ro的毁灭,而且在这座城市有不少似是被杀戮的遗骨。例如,在Mohenjo-da!ro下城南部的一所房屋里,发现有13个遇害成年男女和儿童的骨骼横躺竖卧,杂乱无序。同时,被杀的人中还有一个头盖骨上有146mm深的刀痕,大概是被入侵者用剑砍杀而死的。故可推论:Mohenjo-da!ro是被入侵
溃决。同样地,哈拉巴文化区的其他城镇也遭到了或轻或重的破坏。
外族入侵渐灭说:这是把文明衰落归结为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内部阶级关系紧张,人们对自然规律
无知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水土流失,河流改道,雨量减少,灾害频频,于是外族入侵。
极致火力毁灭说--文明毁灭传奇:
Mohenjo-da^ro最令考古学家们费解的,还是从遗迹上层发掘出来的骸骨都没有被葬于墓中,是一场大规模猝死之后无人料理的遗体?在第五号房舍第74室中发现的14具遗骸当中,夹杂着一些儿童的遗骨,成堆成片地倒在那里。有的脸朝下,有的横躺着重叠在其他骨骸之上,有的用双手盖往脸,有的扭曲着自己的身躯。发掘者哈格布里斯的考察报告中写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些人都是在顷刻间死于某种突然性的变故。"同样的情景在居民区内随处可见,考古学家们纷纷提出了诸如流行病、大屠杀、集体自杀之类的假设,但有足以在顷刻间一举夺去全体居民生命的流行病
?遗骸上也找不到任何杀伤所造成的痕迹。
几年以前,印度考古学家卡哈博士提出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报告。其中写道:"我在9具白骨中,发现有几具留有高温加热的证据,我很难相信这些痕迹是被人突然袭击并屠杀之后才留下来的。"
这当然也不是火葬。可能是火山爆发?但印度河流域却无火山存在。那么,高温来自何处,加热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在当时的那个世界,是何种力量能用异常的高温使Mohenjo-da^ro的居民"猝死"呢?
正如印度史诗“Maha^bha^rata”的文字:
“空中响起轰鸣,接着是一道闪电,南边天空一股火柱冲天而起,比太阳耀眼的火光把天割成两半……房屋、街道及一切生物,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火烧毁了……”“这是一枚弹丸,却拥有整个宇宙的威力,一股赤热的烟雾与火焰,明亮如1000颗太阳;缓缓升起……”“可怕的灼热使动物倒毙,河水沸腾,鱼类等统统烫死;死亡者烧得如焚焦的树干,……毛发和指甲脱落了。盘旋的鸟儿在空中被灼死,食物受染中毒……”城市的骤然毁灭,正可能是这景象?
提起那个年代人类所使用的武器,人们大都只会联想到剑、枪、弓箭、石制投掷器等等,能称得上是火器的,大概也只有很久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火箭了。
而在印度的古代叙事诗中,竞赫然记载着如此令人毛骨惊然的战况,并且流传至今。这种惨痛的记忆,足以与1945年8月的广岛、长崎事件相提并论。
印度史诗“Ra^ma^yan!a”有一段也是叙述凄绝惨烈的古代极致火力战争的。诗中描绘了一种由"大地所有的元素"形成"本身就散发出火焰"的巨枪,"那绽放出令人畏惧亮光的巨枪一发射,连30万的大军也会在一瞬间消失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在“Ra^ma^yan!a”中,拉玛王与魔王拉瓦那进行决战的场所是一个被称为"兰卡"的都市,似乎就在印度河流域的某个地方。的确如此,因为这儿出现了Mohenjo-da^ro的遗迹。而且,"Mohenjo-da^ro"是信德方言里意为"死亡之丘",而当地人至今仍然称之为"兰卡"!或许史诗所流传的就是印度河古城突然消失的原因
?1922年,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所发现的遗址被命名为“死亡谷地”,但当代不少学者认为或许可以称“核死丘”。考古学家找到了此地发生过多次猛烈爆炸的证据:可假设为爆炸中心的地点的一平方公里半径内所有建筑物都成了细细的粉末。距中心较远处,发现了许多人骨架。从骨架摆放的姿势可以看出,死亡的灾难是突然降临的,人们对此毫无察觉。这些骨骼中都奇怪地含有足以与广岛、长崎核袭击死难者相当的辐射线含量。不仅如此,研究者们还惊奇地发现,这座古城焚烧后的瓦砾场,看上去极像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和长崎,地面上还残留着遭受冲击波和核辐射的痕迹。《摩诃婆罗多》这部古印度史诗,形成于600BC以后,它所记载的事件是
文学幻想?是口述历史?或是族群集体潜意识记忆?难以确认。
英国和意大利的考古研究家达威勃特和威恩山迪于1978年冬前往Mohenjo-da^ro作现场调查。两位考古专家发现了能支持这种假设--Mohenjo-da^ro是古代核战争的战场--的实征:
一處直徑四百公尺的黑色石質的廣場,在石頭上發現了綠色的反射光,非常堅硬但卻非常輕。這一片黑石廣場,在當地人口中稱做「玻璃城」。 广场附近到处都铺着这样发出墨绿色光泽的"黑石",可以解释为玻璃工艺品,也可以解释为所谓的"托立尼提物质"(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托立尼提号"〔即"小男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爆炸时,沙漠中的砂粒就因核爆炸产生的高温而熔化,继而凝固成为一种玻璃状物质,因此,这种新物质便被命名为"托立尼提")。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扭曲成玻璃状的陶片。因异常的高温气体而紧紧附着在砖块上的碎物、被镀成黑色的陶制手锡残片等等。
达威勃特和威恩山迪把千方百计从"化成玻璃的市镇"中带回的材料和标本拿到了罗马科技大学火山研究室,并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得知:
"第一件标本--陶片,曾经受到从外侧向内侧的高温加热然后又急剧地冷却下来,这就意昧着,它曾被最低也有950℃至1000℃的高温加热,随后又受到了急速的冷却。"
"第二件标本--黑石,是由石英、长石及玻璃质形成的矿物,这种矿物的熔解点大约在1400-1500℃之间,可是,从形成了空洞小孔的外观来看,可以判定这应该是在极短时间内由极度的高温所造成的。"
因此,达威勃特说:"我们所以要坚持认为这是核子爆炸的结果,是因为在我们现有的科技水平和研究条件之下,我们所能知道的惟一能够在瞬间内发生热波和冲击波的爆炸物只有核武器。"
两位专家在对Mohenjo-da^ro的考察中,发现了许多足以证明这座城市曾发生强烈爆炸的证据,如,刹那间崩坏的砖体建筑物的痕迹、因高热而烧坏的砖块、露天炊事场中大量的非同寻常的生灰等等。他们根据所有那些离奇古怪的迹象推测,在遥远的古代,在Mohenjo-da^ro的上空,曾有比广岛原子弹小型的、核当量约为数千吨TNT的核子武器发生爆炸。
Mohenjo-da^ro这座文明古城至今仍然萦绕着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是谁发动战争?为何发动大战?建造Mohenjo-da^ro的人们从何而来,又向何处而去了?而毁灭这座古城的另一派势力,竟至于令此地的居民感到这般恐惧,难道他们的文明程度比后者还要高出许多?
1-1-3. 先住民文明继承者
虽然雅利安人在远古以前早已进入印度,但大约直到公元前20世紀中雅利安才集体地由Hindu Kush(興都庫什山)穿越帕米爾(Pamir)高原湧入印度河流域,徵服
各个先住民城市。雅利安在進入印度以前是游牧部落,主要崇拜人格化的自然神和祖靈,實行火祭和蘇摩祭,但不是后世所谓的瑜伽内火与禅悦仙液,因为策马中原的游牧民族根本没有瑜伽内观的观念。他們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並和當地先住民民族混合後,渐渐過渡到農業社會。在Aryan的氏族公社中,父权占统治地位,强调洁净而排斥lingam信仰,将之与肮脏-暗肤色相连接。可见后世的Tri-mu^rti几乎全是受先住民影响产生的概念。
公元前10世紀中葉雅利安徵服者才又從印度河上游向東推進至朱木那河;
恆河流域。在這個時期,次大陸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有了重要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加速了社會的分化,過去以血緣為聯係的村社變成了以地域為聯係、由若幹村社組成的農村公社,隨著階級的分化和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印度最初的國家形成了。以《梨俱吠陀》為中心內容的吠陀宗教為了適應上述變化,開始進行重大的革新,出現了以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為二大綱領的婆羅門教。
恒河文明:吠陀时期
约1500BCE,来自东欧与中亚之间的草原地带的一支民族,侵占了印度河流域,史称“Indo-Aryans”(印度雅利安人)。“雅利安”出自梵文“A^ryah!”(贵族)。这些人与当今地中海人同属印欧语系,但是受印度河文明的影响而印度化了。Indo-Aryans文明
在诗书整合时代前可大分为一音誦传时代、多音圣传时代:
| |
一音誦传时代 1800BC~1000BC |
多音圣传时代 1000BC~600BC |
| 地区 |
旁遮普、北方邦西部边缘 |
恒河上游平原、北方邦西部、拉贾斯坦 |
| 经济 |
畜牧为主,无贸易、城市 |
以农业为主,畜牧为次 |
| 器具 |
|
铁器已普遍使用 |
| 政治 |
经典常常提到部落,从未提到部落地区,王位似已世袭,但无专制权。 |
出现区域王国迹象。
|
| 种性 |
期经典很少提到家庭,社会仍属部落性质; |
部落社会分解为4个瓦尔纳的社会。4个瓦尔纳中首陀罗为最低层,吠舍为中层,刹帝利和婆罗门为上层。 |
| 宗教 |
宗教为自然力的人格化,祭祀尚无礼仪程序; |
梵天为最高神,动物神居重要地位,在祭祀中大量杀牲,婆罗门创造祭祀程序。 |
1-2. 先住民原型传承
雅利安人的入侵实际是一个崇尚父权的游牧民族对一个信仰母系文明的农业民族的镇压。《梨俱吠陀》中记载了这场战争;记载了雅利安人摧毁了无数的城市。一被镇压了的文明民族,虽然它不能不屈从于统治者,可是他们的优秀文化往往不会轻易的灭绝;只是成为潜流。这样的事情在印度确实发生了。比如: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一部新的《吠陀本集》,叫《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它虽名为《吠陀》,实则传承着另外一种文化(“其教则必甚古,且其思想有早于《梨俱吠陀》者”——汤用彤);它被名为《吠陀》,显然这是在野文明同化雅利安统治者的结果。《阿达婆“吠陀”》里女神崇拜多于男神,而《梨俱吠陀》以男神为主。《阿达婆“吠陀”》里大量使用密咒,这是它的一大特点。《阿达婆“吠陀”》具有明显的母系文明特征。《阿达婆“吠陀”》体系的文献也被收入了《奥义书》;最著名的是《蛙氏奥义书》(Mandukya
up.),又译为《唵声奥义书》。这部《奥义书》是解释《阿达婆“吠陀”》的密义的。
母系社会的人们倾向于认同内在的血缘关系,易于形成具内向性的、具有行为主体性的性灵观念;父权社会的人们倾向于认同外在的机制关系,易于形成外向性的、异化(把心灵中的原型视为外在独立的神祗,于是自己反而不是行为的主体)的神灵观念。
印度社会圈在雅利安人成为权贵阶级之前的文化传承,在西方印度的Harappa^文明最后阶段主要是Dravida民族的文化传承,而东方则不一定是一样的组成。Harappa^文明遗址显示其文化与雅利安父权文化有明显不同,可假设这先于雅利安的宗教文化是较人本、内在化倾向的,所以在原型传承上两者在印度史上自然形成一明一暗的辩证。
雅利安入印后,
由西向东逐渐将雅利安权贵意识带到恒河流域,诗书整合时代结束前在东方雅利安权贵文化仍未真正成立--纯雅利安人与其信仰仍未居东方印度的统治地位。所以,印度思想
在每个阶段,都是雅利安权贵与先住民大众两者的原型传承体系之间的辩证融合,所以每阶段的思想革命都包含两面,一是先住民大众原型传承体系的浮现,一是雅利安权贵原型传承体系的极化因应。两面之间展现了许多的冲突处,也展现了各别的圆融点,在圆融统一的点上产生新的智慧传承。
在早期的吠陀文献里经常出现雅利安人与一个叫“Da^sa”的民族打仗;雅利安人总是胜利;Da^sa人总是失败。最后Da^sa这个词在梵文中就转成“奴仆”义。但是到了后期的吠陀文献,Da^sa这个词作为部落名称的记述就没有了;而出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词“Nisadha”,并且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这也是个部落的名字;它是生活在恒河边的住在森林里的安居乐业的民族。后期吠陀文献经常提到这个林居的氏族部落;经常提到这样一种生存形态。而雅利安人没有和他们打仗。当雅利安人向东推进到恒河流域时,他们之间是相互宽容的。这就暗示着在恒河流域
森林保存着一些先住民文化,此文化在《奥义书》时期受到部分婆罗门的敬拜(尤其由于静坐玄奥)而进入了婆罗门圣传(记忆)中。当雅利安人在印度完成了由游牧状态向定居状态转变之后,恒河林居居民的生活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反映在后期的婆罗门教的“四行期”思想中。
在哈拉巴民居中挖掘出了无数的女神像!最早的女神雕像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制成的。几乎在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现都能有这么一个结论:大约在距今四千年以前,特别是距今五千年的时候,人类普遍生存于母系社会之中;从距今四千年开始母系文明衰落了,父权文明上升了;到了距今三千年左右,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父权得以确立。哈拉巴发现的大量的女神像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当时在印度河流域生存的这个定居的农业社会属于发达的母系文明。
在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一件武器!我们因此可以推测:这不是一个强权国度,而是一个祥和安宁的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出土了几枚粘土印章。印章上有人形莲花坐姿像,还有各种瑜伽(Yoga)姿势。东方内省修行为主要特征的印度宗教,在这里找到了源头
。可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破译。
1-2-1. 《婆罗门诵》中的先住民影响
雅利安在2000BC从印度的西北方入侵印度,之前处于中亚而没有语言,只有吠陀诗篇的口传。这是有证据的
,例如在考古中发现古中亚地区的丧葬祭品许多符合《梨俱吠陀》的描述。这显示:《梨俱吠陀》里边有些内容是雅利安进驻印度后受到先住民影响而补入的。
另外从语源学也能证明雅利安人是从西边外来的民族,梵语(Sanskrit)与欧洲语言是同一个语系——印欧语系。
1000~900BC左右,出现了注解Veda的《婆罗门诵》(Bra^hman!a)。其中最著名的是解释《夜柔吠陀》的《婆罗门诵》叫《百道婆罗门诵》(Satapatha)。在《婆罗门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梵”(Brahman中性<Brahma)的概念。梵不是诸如Indra,Agni等某个神,而是抽象的
至高实体。这若不是新产生的概念,就是先住民思想的浮现。
吠陀“祭祀”原本是为了取悦神,人格神是根本。但《婆罗门诵》“梵”的概念的提出,使“祭祀”意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祭祀”本身具有神圣意义。
当神力可被“祭祀”支配,原本的人格神原型就已经被革命而走向了超人格神或超位格神(容易被混淆为无神论),这显然与Tantra的概念接近,所以,若不是新产生的概念,就是先住民思想的浮现。
原本雅利安的人格神信仰是比较方便保护特权阶级的,而先住民的Tantra文化(超人格的感应)则具有某种大众平等性的,但
雅利安吠陀化之后为了保持阶级利益,不得不将原本人人可作的祭祀变成某种特权。所以《婆罗门诵》
祭祀必须由专业人士来进行了,借此拱出了一个专门祭祀的阶层——婆罗门(Bra^hman!ah![+])
,于是婆罗门教诞生了--三信条也同时确立了。婆罗门教的诞生,把社会划分了种姓(Varna)。婆罗门教的权力观念--阶级神权、男尊女卑,与先住民的Tantra观念,应该大相径庭。Harappa遗迹显示了母性崇拜、社会平等的痕迹。
作为“一音誦传时代”印度文化圈口传脉络唯一依附的主流"R!gveda"并没有S/iva的观念
,祂在日后的印度教却成为重要神明。而且史诗神话原型传承体系中S/iva的愤怒尊(Virupāksha)、兽主相(Paśupati)、创生力
相(Urdhva-linga)等对"R!gveda"而言似乎是新创意的意象,其实都已表现于Mohenjo-da^ro的一些印章中
了。
1-2-2. 《奥义书》中的先住民影响----见“奥义书时代”一节
800BC进入“奥义书时代”之后,西印度属于先住民大众文化暗流正式浮现台面了。
1-2-3. 沙门思潮中的先住民影响----见“诗书整合时代\沙门思潮”一节
1-3-0. S/iva原型--先住民大众的
大致上,Brahma是代表雅利安权贵原型传承的,S/iva原型是代表先住民大众原型传承的,Vis!n!u是代表诗书整合时代原型传承体系的。
公元二、三世纪出现的Tantra流派,自称传承的是远古的母系文明,反对婆罗门教。虽然与沙门文化一样反对Aryan文化,但Tantra教派不主张禁欲。在修行上Tantra不只是在心性上作禅定,而是要唤醒生命的Sakti(“性力原能”),使之与S/iva结合。这种修行的方法强调身体修炼,Mantra的运用等。在修行结果上以获得悉地(Siddhi—Attainment
of supernatural power)和颇伽(Bhoga—Experience of supernal
pleasure)为境界;有84 Siddha之说,具有强烈的母系文化的特征。Sakti就被比喻成一个女神;没有她,S/iva就失去能力;认为这种母性的力量是万物之源。甚至在有的Tantra经典中视一切女人为女神!Tantra在
世俗上也是女券的维护者,有很多女上师。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在克什米尔地区出现了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阿毗纳瓦笈多(Abhinavagupta,代表作:Tantraloka)。
Tantra由于也和佛教一样反对雅利安《吠陀》信仰,于是造成了信徒的合作与混淆,于是大乘佛教产生了Tantra化的传承。佛教密宗,被称为《续部》。佛教《续部》经典大多都能在Mantramarga怛特罗中找到原形和出处!最早来中国传授怛特罗的印度人是五世纪初来华译《涅槃经》的昙无谶
。公元七、八世纪,金刚智、善无畏和不空先后来汉地传密宗。公元八世纪,印度莲花生大师开始把密宗传到西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
佛教“密宗”是以佛教的见地把传承印度河古文化的Tantra融合进来,但是对于众生而言,理上虽圆融无碍,事上却不得不善作分别,在实践上佛教和Tantra的矛盾永远存在,例如比丘戒和密法修行之间的矛盾
。藏传佛教的很多祖师都不是出家人,宗喀巴则以理论清晰而征结模糊的方式揉合佛教的沙门文化与Tantra的文化。
1-3-1. 印度思想暗流中的欲力辩证:阳性原理的解脱道
行持与阴性原理的大自然欢悦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有一段“恒河的起源”说道,S/iva代表的性力令众神惊慌,央求Siva倾泻到恒河,于是有“恒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印度文明很自然地表现了性意象,阿旃陀石窟壁画描绘佛教的一个个传说,多数作品都带有这种风格。著名的卡朱拉霍印度教寺庙群(约建于公元950年-1050年)绕湖而建,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之一。克纳尔科的黑塔,
性意象栩栩如生,大多认为,这些雕刻中的女人是神的女仆(或出生于寺庙之中,或是普通人家供奉于神的处女),艳欲界与苦行界
对照而形成了圆融无碍的一体:现实层面是苦行,但精神层面却是极乐。克纳尔科神庙是印度教性力派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
印度现代文学的女性自然主义,也来自传统启发。传统印度文学主要是从男性角度看女性,印度文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有了大量女性作家,当女性作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自己,印度文学中的女性意象便发生巨大变化。女性进一步回归于印度文化的传统之中,把女性设想为某种能够抗拒当代文明污染的原始力量,女性形象在她们的笔下变成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体。
1-3-2. 印度思想暗流中欲界与苦行界对照成的圆融一体
传说早在公元2世纪,佛教诗人马鸣《美难陀传》就记述了佛陀度化异母兄弟难陀的方法,那是联系了宗教苦行与享乐联系的古典描述。因为难陀的欢爱根性很深,为了度化他,佛陀让他看了天女,难陀对天女的渴望滋长成了上进心--一种“不究竟”或称为“方便”的菩提心,于是心存这种情欲菩提心开始修炼苦行,他极端的苦行和方便导向菩提的情欲心古怪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
,他对苦行的专注使他突飞猛进,当他到达较智慧的心境而再受到点化后,也就超越情欲而真正导向般若智慧了。
佛教中这类故事并不常见,但在转生出佛教密宗却极力阐发了艳欲与修持的圆融;在公元10世纪印度佛教式微之后,印度教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艳欲思想传承。印度教中的性力派不仅崇拜裸体少女,而且将
交媾引入宗教仪式之中。现实生活中,房事也变成一种积极的宗教性的义务。
1-3-3. 印度思想暗流中的欲境
诗书整合时代的神话体系中,爱欲之神Kama是被S/iva的智慧眼焚去身体而仅存精神的。300~500AD出现的印度教典籍犊子氏"Kama Sutra",描述了古印度年轻艺术爱好者沉湎于诗情的精神生活,
研究生活享受与性爱。犊子氏笔下的性爱是艺术、科学,更有灵修的色彩,他号称是在进行了严格禁欲之后才创作了"Kama Sutra",在最后他说,性爱的最高境界是淡然无情,这一点和印度密宗思想密切相关。印度密宗在流俗化之后,
不能照彻自心的惑结却想借由性爱来超越现实世界的冲突,终结激情。妄想经由领悟主客浑然境界就能浮现真我,解脱自我。正是“解脱”这终极关怀上,使印度S/iva信仰中的苦行禁欲与性爱艳情化为古怪的圆融一体。 |